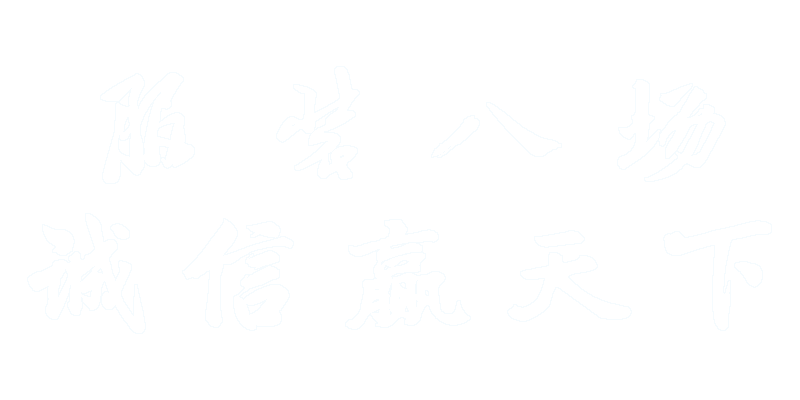傍晚的广州康乐村,刘常鑫含着胸坐在一个小马扎上,面前支着的小黑板还有雨打的痕迹,上面写着:“诚寻客户,代工牛仔裤,长期合作。”这行粉笔字是去年疫情后写的,如今已经有点褪色了。
同样找客户的人就坐在他旁边,沿着康乐桥往西排成一队。有的举着纸板,身上披着样衣,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。

“一整天接不到单也是常态。” 刘常鑫在广州开制衣厂将近20年了,去年疫情效益最差,今年可能排倒数第二。他的印象里,在康乐村,宿舍24小时有人睡觉,厂里24小时有人做工,街上24小时有人下单,可现在不是了。
刘常鑫推掉了一个客户。“单价太低,一天下来挣不到钱,开了机器就要赔电费。”而这个订单是他这周接到的唯一的活。拒绝后,他可以给自己放个假了。
但他没有,依然每天早上提着小黑板,在康乐桥东招工人,下午四五点就把小黑板反过来,去康乐桥西招客户。康乐村里的工人和厂长们管这叫“打游击”。
“万元月薪”的神话
康乐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都在康乐桥周围。桥头一家奶茶店的旁边,十几人围在一起,蹲着的和站着的抽烟聊天,他们都是找活干的工人,感慨着自己干的活不划算,打算挨到晚上等厂长来高价招零工。

“一个月7000块的坚决不干,这都不是钱,”柏德蹲在工友旁边,像个脱口秀演员般说着,“目标是月薪过万!”1987年生的他,在工友里勉强不大不小,但后脑勺的发旋间,头皮已经直接见了光。
5年前从湖北农村来到广州打工,他早已熟悉了康乐村招工的套路:一般越晚工价越高。从晚上11点开始,直到凌晨三四点都有人招工,“真想赚钱的要通宵”。白天,老板找长工,月薪给7000左右;一到半夜,老板有出货急又完不成的单,一小时通常给到35元,工友们干到早上八九点回去睡觉,下午两三点睡醒再出来找活。
宿舍里,工友们自嘲在这打工的都是“深圳三和大神”,“一人干活,全家不愁”,缺钱就干,累了就睡觉打游戏。用柏德的话说,“现在市场不好订单不稳,长工不如零工来钱快”。这时,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,用床单把自己的下铺围上一圈。
宿舍公用的桌子上散放着一摞扑克,有些牌的四角已经翘起。去年疫情解封回到康乐村后,柏德和室友们有空就边喝酒边打双升。打到最后总会半醉半醒地打趣:“谁要是输了就滚回湖北”。但直到今年5月,柏德的宿舍里没一个人走。“赚多赚少都不会走,留在这还有个念想。”柏德说。
晚上九点,康乐村大街上人流如织。柏德走到康乐桥边,从刘常鑫手里接过一件外翻的白色短袖,一只手捻着领口,另一只手搓转边线。这是一件完成了“四线”的样衣,刘常鑫在招人给衣服缝合和锁边,也招剪线、裁床、焊工和车位。
“一件几块?做多少?”柏德问。
“200件,没有次品每件5块5,明天早上四点前出货。”刘常鑫回答。
“6块成不?”柏德把那件短袖抻了回去。
“那走吧。”刘常鑫犹豫了两秒。
刘常鑫的工厂在康乐桥东边200米左右。一幢临街楼的4层,不到100平米的两个房里有13个工人。柏德在机器前坐下来,从地上拎起一块布料开始车“四线”,顺着轨道的卡口把布送进去,脚踩着踏板,机器的咔嗒声和秒针转动的声音错落地响着。
定肩膀,裁剪领子,缝合衣服的前后两片,柏德做完一件大约需要2分钟。“时间有点紧”,但是柏德没有再放弃。按照要求,他要在工位上连着干6个多小时,才有可能在4点前把货做完,赚到1200块。

从招工、讲价到试做,整个流程下来半个小时不到。“他还算熟手,难得。”刘常鑫说着,把小黑板放在车间门口,去隔间里看成衣有没有质量问题。
在康乐村办了20年制衣厂,刘常鑫最骄傲的,就是留住了厂里的13位固定工人,他们跟着刘常鑫跟了十多年了。只有客单量大,又需要24小时内出货的时候,刘常鑫才会去招零工来补补人手。
但刘常鑫其实并不喜欢招零工。每次不得已要招,他都要时不常过来监督,长工的工作质量更让他安心。如果有短工在厂里,他都不敢把手机放在车间,更不用说现金。刘常鑫说:“如果招短工,我会想尽办法让他变成长工。”所以每逢过年他都给工人包车送他们回家,平时有空也一起吃饭。
不过柏德并没有留在厂里做长工的意思,因为他知道,长工夜里没有加班费,一旦做长工,万元月薪就没希望。刘常鑫也承认,康乐村里长工夜里加班就是一种义务,免费加班。“如果给长工加班费,这里开厂的老板迟早要跑,更不用说五险一金”,他也知道劳动法,“可这行一百个工厂里可能只有两个厂能开”,还不包括他自己。
曾经也有工人在他的工厂里拿到上万的月薪。一对夫妇一个月做了4400件衣服,平均单价大概6.3元。刘常鑫开始敲打计算器,一串数字26592弹在屏幕上。“这还是按照最低的算的,准确来说是两万八千五。”

这对夫妇最终没有在刘常鑫的工厂里继续做下去,去年回了湖北老家。刘常鑫常鑫猜测他们可能太累了。忙的时候,除了8小时的吃饭睡觉,其他时间都在干活,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。只有没货时,刘常鑫会主动让他们休息一个班,而且工人之间会错开休息。“长期做下去这是谁都受不了的,包括我自己。”刘常鑫说。
疫情也给厂子和刘常鑫自己都按了暂停键。去年,康乐村刚一复工,刘常鑫就开车从荆州回广州,他庆幸自己基本都做稳定的“内单”,卖给广州沙河、十三行和万佳的国内市场。“大塘那边做外单的就比较惨”,刘常鑫听朋友说,八成的出口外销都毁约了,小厂子不开张,工人全都卷铺盖走人。
厂里的工人,在刘常鑫回广州后几天也到位了,主力是像柏德一样的80后,90后甚至还不如70后多。每次下楼拿外卖时,他总感觉90后都去送外卖了,要么就是运快递,或者去当滴滴司机了。但他也说不出来制衣和送外卖相比有什么好,只是说“各有各的不容易,都是用时间把钱磨出来的”。
喜欢自由,也是他安慰自己招不到年轻人的理由。90后在他眼中,不像70后和80后,要么年轻的没有小孩,要么有老人帮忙带娃,自己出来赚点钱。“不会做衣服的技术,还想赚上万月薪,又感觉做服装没前途,最后只能去送个外卖、快递。”他不认同年轻人的选择,但也承认自己想去个高档小区做保安。
2019年,刘常鑫在朋友圈里转过一篇“深度好文”,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落后产能,吸引不了现在的年轻人。当年,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提到,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下降了0.5个百分点,16~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25%左右。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2018年减少了118万人,下降2.6%。
他也不知道康乐村里这些纺织机还能开多久。只是这两年在抖音里越来越频繁看到,认识的供货商开始直播卖布,也有人发了个自动制衣机的短视频,定位在佛山某制衣工厂,22秒生产一件T恤,24小时不断电生产。他内向,不爱互动,但那次他确实点了个赞。
“服装行业,好像就是一种饱和的状态。”他说他没什么信心继续办厂了,更不想上进了。现在的收益虽然比疫情期间好些,但只有做一些特别的衣服才能赚多些,可他不知道什么衣服叫“特别”,只知道别人喜欢就叫“特别”。
湖北人的去与留
刘常鑫有抽烟的习惯,但是只抽细烟,他说抽烟是有点寂寞,又怕粗烟杀伤性太大。平时抽15块一盒的长白山777,有人来就拿出33块的钻石荷花烟招待。他很少拿钻石荷花出来,因为这是他老乡回湖北前送给他的,他想留着做纪念。
20年前从湖北来到康乐村的刘常鑫,也只赶上了广州服装制造业的第二个十年。90年代中大布匹市场形成,给制衣提供了原料。邻接的康乐村管理宽松、土地廉价,大量流动人口涌入,做服装加工。到2010年,0.46平方千米大小的康乐村,已经聚集着上万家的制衣工厂。

刘常鑫记得这里务工的最初有“三大集团”——江西人、四川人和湖北人。后来江西人把工厂带回江西了,四川的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活做了。只有湖北人,尤其是荆州人,还在这里。
“与其说我们还在康乐村坚守,不如说我们事实上已经落后了”,刘常鑫扫了一眼周围的厂房,不进阳光,机器轰鸣,潮气混着布臭,没人讲话。“这种环境和工作节奏能挨几年?留下就是牺牲。”原先广州发往湖北的大巴隔日才有几班,现在路边大大小小的客运公司都全年发车。
刘常鑫的厂里很多工人都背景相似,要么妻子孩子在湖北老家,要么夫妻俩一起来广州打工赚钱,每年春节才回去一次。不像柏德,他们求稳,就在刘常鑫的厂子里做固定工人,才算熬过了去年疫情。
今年他们还住在一晚20块的床位上,条件稍好的夫妻舍得花50块睡单间。不过他们不怎么吃10块一份的粿条,或12块的猪脚饭了。刘常鑫买了一口大电饭煲放在车间,工人们的碗在旁边摞成一摞,老板娘每天提前完工来给工人做饭。
“离开的也很多。”刘常鑫提到工人离开回湖北时,用上了“挣扎”的字眼。他原来的工人老乡里,有人回家开工厂了,也有人开餐馆、搞建筑,还有人改行学烘焙,目前在做蛋糕。
“当初和我一起来打工的,也有搞得不好的,都去世了”,刘常鑫擤了擤鼻子,皱纹里挤出点笑,“是脑充血、脑梗”。做服装工人熬夜都是常事,直到现在,刘常鑫厂里的工人都是半夜12点下班,刘常鑫自己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2点。他害怕自己也出事,因为他父亲也是因脑出血和脑梗去世的。
客运公司的人也知道,工人回湖北最多的还是去年。疫情下外贸单都停了,工厂没法开张,工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湖北,有的甚至把床都拆了搬走。他们在广州多待一天,就多一天的开支。哪怕是20元一晚的床位,和7块一份的肠粉。去年疫情前,刘常鑫还见到村里有卖湖北监利炒饭的地摊,武汉一封城,招牌上的湖北俩字就没了,后来更是连摊都见不到了。
疫情以来,刘常鑫越来越不喜欢别人叫他老板,他只觉得自己在负责一个小工厂,甚至是小作坊,给客户打工。如果哪天不想干了,就直接转让出去,卷铺盖回老家,和普通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如果有湖北老乡问他广州的工作,他也不建议老乡来康乐村做服装。要是他的好朋友来问,他倒不会直接说回湖北、回村里,“去其他城市开个小店,或者在广州找个其他什么工作干,都比来这里做服装强了”,他说他会这么回答。
但是真正来了的人,大多还是在这留下了。柏德坦言,如果回到5年前,自己还是会选择来到康乐村,不仅是因为身体年轻,也因为能比在湖北赚到更多。
对孩子,刘常鑫也希望他们留在广州,别回农村。刘常鑫25岁的大儿子之前在广州读书,去年回了武汉,给一个汽修美容公司打工,没再回来。刘常鑫说是自己想把他赶到武汉,去学会独立,去体验社会的艰辛,但他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,没让儿子上大学。
15岁的女儿还在广州读初三,早上6点多去学校,晚上6点多放学。刘常鑫自己每天半夜2点下班回家,早上睡到10点左右来工厂。父女俩见面时,总有一个在睡觉。碰上工厂没事下班早,刘常鑫也少有心情带女儿出去吃顿饭,女儿也会用中考复习推脱。每个月一两次的陪伴,最后“几乎就是一个外卖”。
刘常鑫想过放弃,他不知道今天做了,明天会有什么结果。虽然妻子天天劝他回湖北,但他还是要干下去,没得选择。他说他们70后最难,不会种地,农村家里种地的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“自己五十多岁回家太早了,在外面干又有点受不了了。”何况现在康乐村面临旧改,有房产的人大多待价而沽。
“广州会把我送回湖北”
采访时,窗外突然响起火警消防车的声音,刘常鑫没有回答问题,从椅子上一激灵蹦起来,侧身把头探到窗外。等到消防车消失在康乐桥另一侧时,他叹了口气跟工友说:“又一家倒霉了。”害怕听到火警鸣声,是他20年制衣积累下的职业反应。他也曾梦见,一场火把他的所有都毁灭了。
2002年底来广州前,刘常鑫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年。1992年,看了电视剧《外来妹》,他也跟着打工潮坐火车南下。车站买不到票,就从票贩子手里收。出了广州火车站,再坐大巴到深圳的布吉镇,他在那里给别人打地基,刘常鑫说在农村这个叫“挖墙脚”。
刘常鑫第一次做服装是1998年上半年,他去了北京丰台。但一天18个小时的工作很快就搞垮了他的身体,也是他第一次放弃。他又一次来了广东,在东莞的虎门打工攒钱。直到2002年借了一笔高利贷,他才凑够钱,在广州鹭江的停车场旁边办了个厂。当时办厂价位很低,“两万两千块左右,就可以办一个小型工厂”。
可非典就在那年年底暴发了。刘常鑫感冒了两周,工厂也两周没有开张,“每天就睡在车间里靠窗通风的地方,趴在地上动都不动。”后来,他才鼓起勇气去鹭江疾控中心抽血检查,没有感染。去年疫情,他留在湖北荆州老家,距离武汉两小时车程,新冠确诊人数略高于浙江省。“不赚钱不行,但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要。”刘常鑫感觉自己已经没了非典时的血气方刚,虽然头发是黑的,但心里白发苍苍。
两年前,刘常鑫才从住了18年的厂房里搬出来,和妻女到康乐桥边的一间二手房里住。厂房楼下是珠宝店和百货超市,白天是销售的喊叫,到晚上音响就放抖音神曲,想在这好好睡觉是一种奢望。让刘常鑫下定决心的,还有厂房的空气。年轻时没感觉,现在他看到灰尘都怕,感觉这空气从别人口里吐出来,自己再吸进去。

搬新家一事上,刘常鑫没声张,甚至不大愿意邀朋友来。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办厂的人早已住进了小区房。“隔壁逸景翠园的房价,我看着它从五六千一平米,涨到四万多。”刘常鑫还记得,当年和两个朋友斗地主到半夜三点,散伙时朋友说“去逸景翠园买房子咯,常鑫你去不去?”他一口拒绝,想着有钱了回家自己盖一栋房子。如今他后悔了。“我现在奋斗也好,不奋斗也好,还不如当初一咬牙买套房子”。
虽然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康乐村,和工人一样,刘常鑫并没有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。除了去番禺交货,刘常鑫几乎都在康乐村里,甚至没有去广州其他地方逛逛,他只知道,很多外地游客都去上下九去玩,“十三行的一些散货就在那卖,十几二十块一件的那种”。
康乐村制衣行业的从业者大多和刘常鑫一样,虽不知道广州“好在哪里”,但很想努力留下来。刘常鑫的朋友林安和他一样在2002年来康乐村开制衣厂。2017年左右林安就感到好像到了瓶颈期,2020年疫情更几乎没赚到钱。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打印了很多张红色的转让广告,最后还是咬着牙没贴出去。在4月底一次聚会,林安才发现刘常鑫和自己一样,年底都打印好了转让广告,而今年又不贴了。
这座城市留给刘常鑫的记忆,大多和制衣有关,但他依然说,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广州。
“我想留在广州,但现实是残酷的,它会把我送回湖北。”
说罢,刘常鑫又点起了一根细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