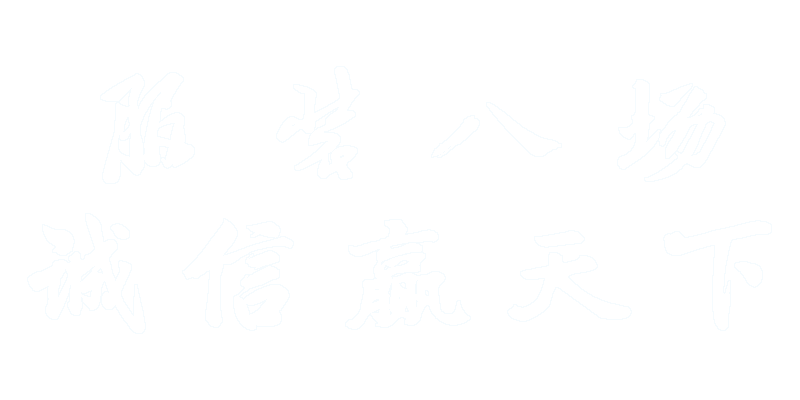上午9点,广州康乐东约南大街一家快餐店里,30岁左右的服务员坐在矮凳上,手里熟练地削着茄子,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热闹的招工场景:几十个制衣厂老板一手拎着样衣,一手举着工位需求的纸板,肩并着肩站着,从康乐桥往东绵延七八百米。
老板的对面围着上百个工人。这百来人挤在一条宽五六米、长不到一公里的街巷里,挑着不同类型的衣服。这一挑,将决定工人这天会去哪个厂,做哪道工序,以及挣多少钱。
不是万不得已,电动自行车都不敢随便驶入。载着布料的小货车实在避让不开,得一路鸣笛才能挤出一条“生”路。如此盛况在康乐村、鹭江村持续了有近20年。如果没有一纸规划,这样的场景可能还会延续很多年。
12月4日,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挂出了广州海珠区凤阳街凤和(康乐村、鹭江村)更新改造项目公告,改造范围内总建筑面积335.94万平方米,改造投资总金额约为346.67亿元,其中复建安置资金约250.77亿元。
这是广州城市更新挂网招商以来,截至目前投资总额最大的旧改项目。如果一切顺利,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安置地块上的房屋拆卸。
不停运转的纺织机声音,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此停下。
“拆只是时间问题”
凭借临近中大布匹市场的地理优势,鹭江村、康乐村成为广州地区制衣业最大聚集地之一,估计有超过1万家店铺、超过1万家制衣厂,聚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,95%以上是外来人口,且大部分人来自湖北,因此被称为“湖北村”。
一条纺织产业链,在“湖北村”形成了一座不夜城。
布匹市场和制衣厂距离短,交货周期也就一两晚,这里成了24小时不停转的大型制衣工坊,老板忙着招工,工人忙着赶工。
逼仄的车间里缝纫机不停运转,昏暗的仓库堆满了刚成型的衣服,运着布料的电动车在窄巷里飞速驶过,地上的碎布料、棉絮、垃圾随风扬起,若不是戴着口罩,路人都得捂着嘴走。
200平方米的制衣厂不算敞亮,对于工作环境,老板周闻(化名)不太在意。他的眼里只有工期,盯着30个工人手里的进度,心里做好了打算:到深夜还做不完,就去外面再招几个临工,“凌晨两三点,还有大把人守着等”。
深夜的等待还能持续几年。
根据公告,鹭江村、康乐村改造方式将通过合作改造模式对旧村庄全面改造。待用地手续完善后,合作企业按照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规划,拆除重建实施改造。
具体至实施时间,2021年6月30日前将完成片区策划方案、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审批;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安置地块的房屋拆卸;2023年12月31日前全部安置房开工建设;2025年12月31日前将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。
“这次即使真要拆,也不会那么快。”在这里工作12年的周闻嘴里这么说着,但他也深知,“拆是肯定的,只是时间问题”。
“湖北村”大大小小的告示栏里,贴满了“制衣厂转让”的告示。在这个追求效率的地方,逐利的老板比谁都更容易嗅到利益的味道。
拨打了多个转让电话,制衣厂老板各有不同的说法:太累了不想干,赚不到钱;想把小厂房换成大厂房。转让理由虽有不同,但对旧改的想法都是一致的,“旧改涉及拆迁赔偿问题,至少五年拆不了”。
“我们就是最后一波接盘侠。”周闻2014年花了20万元转让费盘下这个厂房,现在订单稳定了,也就想换个更大的,但他知道现在厂房肯定转不出去。“旧改对想租厂房的人和准备转出厂房的人肯定是影响最大。想进来的人不敢进,明知道这里要拆,就不会再顶手厂房。”
顶着“最贵旧改”的光环,湖北人在“湖北村”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。
“只要不低于20万元,我都愿意转让!”湖北人陈春虎花了23万元拿下200平方米的厂房,想换300平方米的厂房扩产多赚点钱,但转让广告都贴出去两个月了,还没能转让出去,“本来可以开价35万元,现在因为拆迁都压下来了,结果还没转出去。”
制衣厂老板在压缩利润空间,打工者在担心生存空间。48岁的湖北荆州人秦凤兰给一家制衣厂工人做饭,一个月收入2500元。她反复确认:“这里确定要拆了吗?什么时候拆?拆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?”
“重建一个祠堂就行”
这一片土地,不仅有湖北人赖以生存的机会,也是本地村民重生发展的机遇。
1993年,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鹭江村,租下民宅做加工厂:二楼加工,三楼住人。村里加工厂日渐增多,出租屋供不应求,村民洗脚上田,大规模加建楼房,由原来的三层半加建到五六层。租金几乎成为村民所有经济来源。
如今,旧改似乎给这里一个新的发展机遇。公告显示,项目有明确产业导入的内容与要求,保证项目建成后产业导入有实质性成效;竞得人还需承建华盛南路道路大修工程、叠景路临时维修工程、凤江小学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、客村小学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、逸景第一小学本校区校园综合改造提升工程等。
对本地村民来说,旧改自然是双手赞成的。
“肯定想旧改啦,上面要怎么改,我们就怎么做。历史的车轮都是滚滚往前的。”12月12日下午,一位本地村民在祠堂内说,“我们只有一个要求,就是拆完祠堂后,要帮我们重新修建一个。”
数十万个来往其中的湖北打工者,只是他们在“湖北村”的身份标记。再丰富或再枯燥的故事,早被这里的生活同化,就如一件件绝无二致的成衣,加上密封的包装袋。无论旧改与否,它们都不属于这里,迟早要被送往远处。
“要拆就拆吧,赚的不是我,亏的也不只是我。”周闻知道,“湖北村”旧改跟自己最有关系,但也最没关系。“在这里,我们没有安身的地方,心不稳,没有归属感。”
对他们来说,这里离生存很近,但离生活很远。
“买不起附近的房子,买到周边城市也不太现实,不可能每天跑来跑去,只能一心想着,赚到钱了回老家。”周闻笑着说,“只能拼命地工作。但灵魂在哪?肯定不能安放在这里,安放不了的。你说,归属感从何而来?”
但有人依依不舍。“还是有感情的,我在这打工20年,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,舍不得离开。”正在找临时工的湖北人胡希说,真要拆也只能到其他地方去,“没办法,我们也要生存。”
“大环境就是这样,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,对我们工厂来说,也是没有办法,只希望政府能帮我们做个规划,比如说整体搬迁至某个地方重新生产。”周闻说,“对我个人来说,还是比较遗憾,从青年小伙变成油腻大叔,所有青春都在这里,只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创业了。”
周闻的打算是做一天算一天,“我们船小好调头”。明年,他要在房顶做一个隔热层,再装两台空调,拆掉一间办公室,加装八九台机器,需要投入五六万元。“客户稳定,肯定不会亏本,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,现在想在拆之前,能多捞点就多捞点。”